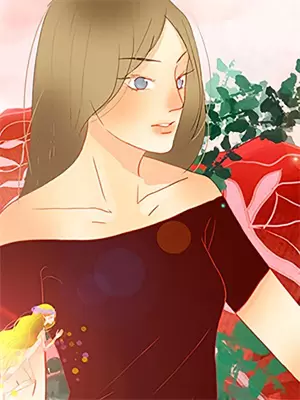
大婚那夜,他带花魁入府,我独守空房。他辱我、欺我,说我配不上正妻之位。可转头却说,
从始至终,心里放不下的只有我。我轻笑一声:“你倒真是有病。”1嫁入谢家,
是我五岁那年便定下的命数。可今夜,红烛燃尽,新房冷寂,新郎却迟迟未归。
我枯坐至寅时。听喜婆打盹的鼾声,听宫灯将熄未熄的微弱轻响。忽然,
窗外传来丫鬟们压低的窃窃私语:“世子爷竟真把那花魁带回府了,可真是怜香惜玉。
”“新妇独守空房,啧,真够可怜。”“她算哪门子新妇?世子连面都懒得见。
”“若我是她,怕是早就羞愤而死了。”我轻垂眼睫,默然拢紧袖口。
她们只道我被弃如敝履,却不知,我并不甚在意。嫁与谢珩,于我而言,
不过是一步不得不走的棋。母亲旧病缠绵,姜家式微。父亲那点伪善的疼爱,
早随外祖父倒台烟消云散。我唯有嫁入谢家。为母亲,也为自己。手指轻轻敲着床沿,
窗外的戏谑议论渐渐远去。这后宅之中,不受宠的女子如何煎熬,我比谁都清楚。
可真当身披嫁衣,坐于红帐之内,我心中仍是难以平静。谢珩自幼便不喜我,桀骜凉薄。
他不来,确实清净。但明日,今夜之事必会传遍京城。母亲知道了,会如何伤心?
胸中忽然涌起一阵无法抑制的烦闷。为何连这点薄薄的体面,他都不肯予我?2天色微亮,
杏儿便掀帘入内,手托一盏参汤。“少夫人,时辰快到了。”“须得请世子爷起身,
与您一道敬茶才好。”我抬眸看她,未作多言。独守空房已是莫大的羞辱,
敬茶之礼若再出差池,只怕更成笑柄。起身更衣,略施淡妆,脂粉掩去眉间倦意。所幸,
镜中人气色尚可。我端起汤盏,沿长廊一路而行。院门前,两名小厮瞧见我来,神色躲闪。
我望向院中,丫鬟们远远立于檐下。心头略起疑惑,面上却淡淡开口:“去通传一声,
就说我带了参汤,服侍世子爷起身敬茶。”二人支支吾吾,脚下却纹丝未动。忽然,
屋内传来女子刻意压低的轻笑与窃语,伴着隐约榻板微响。我立于院前,唇边冷笑一瞬。
这般体力,何须参汤滋补?片刻后,内室动静渐歇。只听一女子轻笑,
娇媚而揶揄:“世子爷还要喝参汤么?奴家可吃不消了。”心底泛起一阵难言的厌恶,
半晌无言。终于,房门打开。我步入内室,将参汤轻轻搁于案几之上。屏风后,
红芙斜倚床榻,衣带松松,眉眼媚如春水。谢珩则负手立于窗前,面容冷淡,许久无言。
终是转身,端起参汤浅尝一口。“啪!”汤盏骤然落地,应声碎裂,瓷片飞溅至我裙角。
“姜渔,我倒真是小瞧了你。”我一怔,尚未开口,他便已步步逼近,
嗓音冷厉:“你若想与我圆房,也不是不可。”“将你那块玉佩砸了便是。”我微微一顿,
缓缓摇头。他眼中寒意陡然深了几分,嗤笑出声:“你还真是不要脸到了极致。
”我平静抬眼:“世子此言,何意?”他指向地上碎瓷,语气森寒:“汤里加了什么,
你自己不清楚?”我蓦然回首,门口杏儿垂首站立,手指却绞得发白。
难怪她今晨这般殷勤催促,只怕她也未曾料到谢珩竟留红芙至今。我收回目光,
轻声道:“我不知汤里加了东西。”他冷笑,却并未继续追问此事,
只是神色愈冷:“你竟然真连那玉佩都不肯舍?”我垂眸,低低应了声:“是。”那枚玉佩,
是顾承安留给我的最后一物。我不想,也不能舍弃。谢珩听罢怒意翻涌,猛地一脚踹翻案几,
瓷片四散:“姜渔,你果然好本事。”我默默蹲下,捡拾散落一地的碎片。
指尖被锋利瓷片划破,血珠渗出,我匆匆以袖掩去。望着满地狼藉的男女衣物,
我唇角浮起一丝自嘲的苦笑。若我真有本事,何须在这污秽之地送汤?许是瞧见我指尖血痕,
谢珩更怒。抬脚又踹翻一张凳子,碎片险些溅至我脸侧:“这府里下人都死绝了吗?
”“你不是非要做世子夫人吗?那便做得彻底些,莫要脏了我的地!”我缓缓起身,
鲜血顺着指尖滴落,心底微微发凉。3看他拂袖而去,我犹豫一瞬,终是追上前去:“世子。
”他脚步微顿,却未回头。我拢紧袖角,低声道:“今日之事,是我唐突,并非我本意。
”他肩膀微微一动,似是松了口气,又似压下怒意。我垂眼望向满地碎瓷,
声音极轻:“往后无论世子房中是谁,我都不会再来打扰。”话落,四下沉寂。
他终于回身看我,目光复杂,许久才冷冷开口:“你倒真是干脆。
”他的视线落在我染血的指尖上,我忙掩袖遮住:“不妨事,敬茶时辰将至,
还请世子与我一道。”他静静看了我一瞬,唇角泛起嘲讽,语气既玩味又冷漠:“新婚之夜,
夫君流连外院,你仍体贴周全,毫无怨言。”“姜渔,你当真大度。
”我默然垂眸:“我只是,不想扰你清净罢了。”他一怔,随即冷笑道:“甚好。
”“今日之事,再有一次,便是休书一封。”我立刻应声道:“好,请世子放心。
”他目光复杂,似在等我反悔。但我没有。他甩袖而去,背影渐远。我唇角微微上扬,
却只觉荒唐。他这般,难道竟是对我的“大度”感到失望了?4正厅前,谢珩未曾唤我,
只在前廊略作停留。我快步赶至,他却头也不回,径自踏入厅中。厅内言语渐歇。
太夫人端坐上首,神情端凝。谢侯爷、谢夫人,及各房族亲悉数在列。我屏息入内,
屈膝行礼,先将茶盏奉至谢侯爷。“这手抖得,倒像是头回端茶似的。”二婶讥笑出声,
语中带刺,引得几道附和轻笑。谢夫人则浅笑一声,温声打圆场:“昨夜新婚,
今晨又起得早。”“气色难免不济,也怨不得新妇。”我垂眸不语,只将茶盏稳稳奉上。
谢珩立于一旁,自始至终未曾看我一眼。礼毕,我正欲退下一旁。便见太夫人望向谢夫人,
缓缓开口:“三朝回门之礼,可曾备妥?”谢夫人尚未应声,
谢珩却忽然抢先作答:“三日后我已与故友约定出游,恐难陪同。”我心中一震,
险些握不住手中茶盏。我早料到他会不愿陪我留宿姜家。却不曾想,
他连这点敷衍的体面也不肯顾全。太夫人扫了谢珩一眼,神情未变,
却字字威严:“这桩婚事,是你祖父生前所定。”“既已成亲,礼数自当周全。
”“昨夜胡闹,已伤长辈颜面,莫再添乱。”谢珩神色微滞,面露不悦,却终究未再言语。
我轻轻退至一旁,规规矩矩站好。厅中渐渐恢复热闹交谈。席间笑语不断,
间或仍有几句轻薄言辞指向我,我却已无心细听。半晌,太夫人抬眼扫视众人,
沉静道:“茶已敬,新妇已入门。”“后宅之中,说话行事亦须有分寸。
”“莫教外人笑我谢家教养。”众人连声应是。我低头应诺,心绪微动。那一刻,
我忽然想起母亲。太夫人语气虽淡,却处处护我体面。若母亲也在此,定也会如她这般。
于万难之中,为我遮风挡雨。只可惜,她病重卧床。我眼前一阵发涩,强忍着泪水。
5三朝回门,谢珩勉强随我回了姜府。未见母亲迎出,唯父亲带着弟妹,
在府门前满面堆笑相迎。寒暄几句后,他将三弟留在前厅招待谢珩。自己却将我唤入偏厅。
门一阖,笑意尽敛,父亲的脸色阴沉如水。“你究竟做了何事,惹得世子不快?
”我低头不语。他语气渐冷:“前些日子,世子已允诺保举你三弟入兵部。
”“如今却突然改口,你可知道缘由?”我袖下手指微颤,仍未开口。“连个男人都哄不住,
连房都还未圆,真叫我丢尽颜面!”“姜渔,若不是你娘病着,今日你便去祠堂跪着!
”我咬唇,忍不住轻声问道:“母亲……她,可还安好?”父亲神色略缓,
带着些许敷衍:“已请京中名医,服了几剂汤药,情况好转许多。”“你只管安心侍奉世子,
莫叫他心烦。”我低声应下,心中却愈发不安。回到院中,我欲前往探望母亲,
却被门口丫鬟拦住:“老爷吩咐,夫人服药后须静养,不便见人。”“大小姐,请放心。
”“夫人病情已有起色,待情形稳定,定会通知您。”我点了点头,心口发闷,
终究无言而返。不愿回前厅应酬,便独自绕至花园散心。假山小径幽静曲折,
却被一阵熟悉笑声打破。“世子爷,当真连姐姐的房门都未曾踏入?”是姜念,
她的语气娇嗔中透着试探。谢珩笑着答道:“怎么,吃味了?”“姐姐温顺又乖巧,
从来都是不妒不闹,世子怎忍心如此冷待她?”她的声音柔得几近撒娇,
唯独尾音带着细微的不屑。“她心中装着旁人。”谢珩语气冷淡,带着显而易见的厌恶。
“像那样的女子,我碰都嫌脏。”姜念语带酸涩:“可她那样,还占着正妻之位,
未免太不公平。”谢珩闻言却轻笑一声:“你这般醋意大,倒是可爱得紧。”“我谢珩,
就喜欢你这样的姑娘。”我站在假山之后,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袖口。原来,他喜欢的,
是这般娇蛮明媚、略带刁蛮的女子。那我这一路的隐忍与顺从,又算什么?归府途中,
谢珩在半道弃我而去,径自去了酒楼。我只得独自回府,草草洗漱后便早早熄灯歇息。
天色微暗,昏昏欲睡之际,房门却猛然被推开。我惊坐起身,尚未来得及唤人,
一股炽热的气息便将我压入怀中。耳畔,是谢珩压抑而紊乱的喘息:“姜渔……帮帮我。
”6我心头一紧,下意识后退,却被他一把揽住,力道惊人。“世子怎忽然……?
”我低声问,却被他打断。他喘息不稳,气息滚烫,额间冷汗直冒,面色潮红,
神情有些恍惚。“你不是盼我回来?”他嗓音低哑,带着笑意,“如今……如你所愿。
”他掌心覆上我的手腕,指尖灼人,我察觉不对,借着微光细看——他的眼神迷离,
分明是中了药。我脑中一片混乱,呼吸一窒,鼻端却忽然嗅到一缕熟悉的脂粉香。是桂花香,
姜念素爱此味。我心头一凛,定睛细看。他衣襟微敞,颈侧赫然可见一道嫣红痕迹,
暧昧而刺目。一阵恶心猛地涌上心头,我咬牙推开他,
声音冰冷:“世子不如去寻心仪之人解药。”谢珩动作一顿,旋即低低笑出声,
嗓音哑得发沉:见我不语,他掌心覆上我脸颊:“怎么,吃醋了?”语气竟也温柔下来,
像是在哄人:“难得你也妒忌一次。”“可我偏要你来帮我。”我怔了一瞬,竟有片刻失神。
可下一息,脑中便浮现今日在假山后听到的一切。我侧开脸:“我可以帮你,
但你需答应我一件事。”他挑起我下颌,似笑非笑地看着我,神情带着一种笃定:“你说,
莫不是想让我送走姜念?”“自然不是。”我打断他,
声音清冷:“我只求世子保举我三弟入兵部。”屋内骤然安静。
他眼底最后一丝柔色渐渐褪去,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讥笑。唇角缓缓勾起,
像是听见了极为讽刺的笑话。“姜渔,你果然从不让我失望。”7谢珩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。
他指尖勾起我的下颌,眸底寒意刺骨:“姜渔,你倒是手段了得。”“趁人之危,
也不怕污了你姜家嫡女的名声?”我尚未辩解,便被他一把推开。身体撞上床角,腰间生疼,
只觉脸颊火辣发烫。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,眼底尽是嘲意:“本世子再如何荒唐,
也不至于饥不择食。”“你这样的法子,不配摆在我面前。”说罢,他便吩咐门外丫鬟备水。
“把热水送到净房。”丫鬟应声而退,我却站在原地,动也不动。片刻后,浴房水声起伏,
似有闷声压抑传出。那声音如钝刃剐心,叫人羞愤至极。我指甲深陷掌心,唇齿轻咬,
几欲泛血。可一想到父亲的冷脸,母亲的病重。我终是闭眼,缓缓起身,朝浴房走去。
屏风之内雾气氤氲,朦胧水汽间,隐见人影晃动。我屏住呼吸,
学着红芙的口气轻声软语:“世子,方才是我错了。”“你别气我了……好不好?”话未尽,
水声忽止,屏风之后陷入死寂。须臾,他湿发披肩,随手披了件外衫走出。
目光沉沉地落在我身上,凉薄如霜。“怎么,才入侯府几日,便学得一身媚态?
”“你以为撒个娇,装个怯,就能将我哄住?”他步步逼近,语气愈发森冷。
抬手钳住我下颌,力道狠厉得几近生疼:“说,这套手段是谁教你的?”我别开脸,
努力挤出一丝柔声:“世子想要什么,我都依你,只求……你别再生气。”谢珩一声冷笑,
眼底寒意愈深。手指一松,唇角却带着嘲弄地凑至我耳侧:“姜渔,本世子再怎不堪,
也不缺你这般上赶着讨好的女人。”“你那点子狐媚,不如去哄些下等登徒子,
兴许他们还肯赏脸。”一句话,胜过刀剑穿心。我心中残存的一点自尊,
在这句轻蔑中土崩瓦解。正此时,门外传来丫鬟怯怯的通报声:“世子,红芙姑娘求见。
”“说……若您不肯见,她便一直候着。”谢珩挑了挑眉,似是笑了。他转过身,
目光再次落在我身上。不再冷戾,却带着令人作呕的玩味。“去换件像样的衣裳。
”他指尖挑起我衣襟的一角。语气漫不经心,“替我去请红芙姑娘进来。”“你这副模样,
可莫要吓着人。”8我从谢珩手中挣脱,尚未整好衣襟,便见红芙提裙而入。
她仿若未见我一般,径直闯入主卧,嗓音娇媚,字字带笑:“世子,奴家来了。
”声音里三分娇态,七分挑衅。我立在廊间,未动分毫,心底却已一片死寂。红芙止步榻前,
忽而偏首回望,鼻尖微动,轻笑道:“这香也忒清淡,世子可受得了?”谢珩似是有意附和,
低笑出声,语气懒散而讥讽:“无妨,左右不过是摆设。”一字一句,若微雨入泥,无声,
却凉透。我垂下眼睫,将悲凉隐入深处,缓缓退了出去。门扉甫掩,
内室便有语笑声断断续续传出,低低不绝。红芙娇言软语,谢珩偶尔应声,
两人似在调笑嬉语,分毫不避。我无声回房,坐在偏室那张狭小的软榻上。
耳中动静如锥似刀,刺骨生寒,叫人几欲疯魔。我胸口发闷,几近窒息,终是颤着手,
从袖中取出那枚玉佩。鱼形佩饰,尾翘鳞纹,温润如昔。这是顾承安留给我的最后一物。
我指腹轻触,仿佛抚过他掌心残存的温热。顾承安……若你还在,该多好。
门外忽传来细微叩响,我一惊,忙将玉佩藏回袖中。推门,只见秋霜立在廊下,
是太夫人身边的婢女。“太夫人有何吩咐?”我压下情绪,尽力平稳嗓音。秋霜低头,
将一只妆奁递来,语声恭谨:“这是夫人娘家托人送来,太夫人让您亲自看过。
”我心头倏地一跳,连忙接过妆奁,关门落锁。揭开盖子,一封信静静躺在底层。
字迹潦草却力透纸背:“小姐,夫人去了。”“老爷早将夫人送往郊外庄子静养,
自从那次与您分别,便不许旁人再提。”“夫人知晓老爷只将您当作攀附权贵的筹码,
更知您心中苦楚。”“顾郎君坠崖三载,夫人劝您莫再执念。”“她临终有言,
盼小姐自此摆脱桎梏,自由而活,不必再受人左右。”我握着信纸的手不住颤抖,指节发白。
字字如刀,句句扎心。母亲……竟然就这样去了?今日回门,我几次央求探望,
却被院中丫鬟以“服药静养”为由推辞搪塞。原来,她那时……竟早已不在府中。
我怔怔站着,眼前一阵阵发黑。喉间似哽着碎石,咽也咽不下,吐也吐不出。世间再无一人,
会为我心疼,会替我遮风挡雨。唯余这薄如蝉翼的一页纸,被我攥得皱折不堪。
我望向窗外天色。月光清寒如水,却照不进我心底的荒凉。9我捏着信笺,手止不住地颤抖。
母亲素有沉疴,可在我出嫁前,她还亲口答应我,会好好活着。让我安心,说她会等我回家。
三朝回门时,父亲更是言之凿凿。说请了京中名医,病势渐缓,稳中向好。
可才过去半日……她竟已撒手人寰?一阵突如其来的钝痛从胸口涌起,重重压下,
几乎将我整个人压垮。耳边,偏在此时,又传来红芙娇媚的笑声,
和谢珩低低的嗓音交叠缠绵。如同针锥入骨,声声穿心,将我心口那片柔软撕裂成渣。
门外忽又响起轻叩声,我木然起身,开门。红芙斜倚门框,衣襟半敞。脖颈上红痕深浅不一,
如胜利者炫耀的勋章。她瞧着我怔愣失魂的模样,先是一怔,随即便道:“世子爷说了,
让你去库房取那套舞姬的衣裳。”我怔了怔,一时未能反应:“……什么?”她掩唇轻笑,
“看来少夫人果真不解风情。”“难怪世子爷连碰都不愿碰你一下。
”她目光在我苍白面容上肆意游移,轻慢得毫不掩饰。“你不会真以为,嫁进谢家,
就能高枕无忧地做这世子夫人了吧?”我静静听着,心如枯井,毫无波澜。她却兴致盎然,
转头朝里娇声唤道:“世子爷,您这新妇听说要取舞衣,都快吓傻了呢。
”内室传来谢珩那不咸不淡的一句:“她若肯取,你便叫她日日去取。”我脑中轰然作响,
仿佛有什么在心口炸开。耳中,却恰在此刻响起母亲临终时那句叮咛。“望你自此摆脱桎梏,
自由而活,不必再受人左右。”是啊……我已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辱的小女儿。我缓缓抬眼,
看向红芙,光清冷无波。她被我看得一愣,笑意微滞,却仍不肯收敛:“记得你自己的身份。
”“别真把自己当了这侯府的女主人。”我转身离开,脚步未停,衣角掠起风声。
10回到房内,我换上一身素色粗布衣裳。压低斗笠,悄然出府。街巷热闹如旧,
我却如行尸走肉般游走其中。耳畔一遍遍回荡着母亲的遗言:“渔儿,娘亲不愿再拖累你,
余生你便为自己活罢。”眼眶泛酸,视线模糊。白日里父亲还言之凿凿,说母亲病势已稳,
正请名医调理。可她若真在调养,为何不许我一见?如今细细回想,丫鬟百般推脱,
父亲刻意搪塞……处处都是破绽。刚出巷口,便迎面撞上父亲。他带着几名家丁,神色阴沉,
一言不发便伸手攥住我手腕:“你嫁入谢家才几日,竟敢私自出府?”“如今谢家已有怨言,
你莫非想气死我不成?”我冷冷拂开他的手,抬头直视他:“父亲,母亲已死,
您难道半点不怕报应?”他脸色瞬间煞白,指着我,厉声喝道:“你胡说什么?!
”我嗤笑一声,不再与他争辩,径直唤了马车,往庄子赶去。郊外庄子冷清破败。
母亲生前住的屋舍里,药罐冰冷,门框随风而动。我颤抖着双手,为她整理衣物,
将她亲手入殓。她生前被欺压至此,死后,又怎肯入那姜家祖坟?翌日清晨,山风轻拂。
我将母亲安葬在松岭山巅,那是我与顾承安初见之地。有风,有花,
有她未曾见过的自在与广阔。我跪在坟前许久,直到日落西山,才缓缓起身。回到庄子上,
天色已黑,我却迟迟不愿回谢府。直到谢珩派人寻来,丫鬟冷声传话:“世子爷说了,
三日不归,姜家上下如何,你自负。”我垂眸未语,如何不回?母亲留给我的外祖母遗物,
还有那封信,都还在谢家。入夜归府,屋内早已一片狼藉。丫鬟们远远缩在墙角,面露惊惧。
房门半掩,内室中柜门大敞,衣物被翻得七零八落。谢珩端坐在榻边,
手中把玩一只雕花锦匣,神情凉薄。“你还知道回来?”我心头一紧,目光定在那匣子上。
“把它还我。”他似笑非笑,将匣子扬起:“你藏得倒紧,母亲留给你的东西,我自不会动。
”“但这封信……你怎好意思留着?”我猛地上前,却被他一把扣住手腕。
他慢条斯理展开信笺,低声念道:“渔儿,那日你不肯随我离开,我并不怪你。
”“我知你放不下夫人,也怯于世俗之名。”“但我始终相信,那并非你的本意。
”“待我事了,定来接你与夫人一同离开,你要等我。”我竭力去夺,他却步步后退。
“你宁可藏着一个死人的信,也不肯正眼看看你夫君?”“姜渔,你真是叫人恶心。
”“你若亲手毁了它,我就当没有顾承安这一出。”“只要你肯,我立刻奏请保举你三弟,
亦可助你父亲官运亨通。”我冷笑,字字清晰:“不可能,我从未拿你当过夫君。
”我猛然扑上去,去抢。他反手将我甩开,寒声道:“既如此,那便毁了它。
”“你如此执迷不悟,本世子今日便替你斩断过去。”“死人的信,留着作甚?
”我怒不可遏,顺手抓起桌上的香炉砸向他:“你凭什么碰我的东西?”“承安生死未卜,
他不是死人!”谢珩怔住,像是从未见过这样的我。眼底闪过一丝愕然,旋即寒光乍现,
怒意翻涌。“好一个世子夫人,竟敢砸我?”他拂袖扫落案几,扬手欲将那封信撕碎。
我瞳孔一缩,扑过去跪下。双膝磕在冰冷的地砖上,抱住他的腿,
声音颤得厉害:“谢珩……求你。”“我求你。”他低头看着我,唇角的讥笑却越发凉薄。











